今日导师

郭初阳
独立教师、杭州越读馆创办人,致力于语文课堂的生态改良。著有《言说抵抗沉默》《癫狂与谨守》《大人为什么要开会:运用规则获得自由》《一个独立教师的语文之旅》等;
注:脚里学院第七期山乡教师成长计划将于11月在上海举行,主题为“行走与写作”。郭初阳老师作为本期的特邀导师,将会在11月6日上午与44位乡村一线教师共度一场独特的写作之旅。
本文是郭初阳老师的二十多年的大学挚友,同为脚里学院特邀导师的蔡朝阳老师所写。本是希望郭老师能推荐一些他的观点著作供参训的老师提前熟悉,不料郭老师却推来了这篇。蔡老师写郭老师,没有太多华丽的赞美之词,多是些看起来日常的平平淡淡,却处处见真情。借蔡老师之笔,让我们看到一个简约沉静的郭老师之外,也对蔡老师更加熟悉起来。
如果再上一次大学,我还是选择跟郭初阳同学吧
文/蔡朝阳
郭初阳现在是越来越简朴了。他的新书装帧接近极简主义风格,就跟他的生活一样,不事奢华,返璞归真。有一段时间,他还成为了素食主义,简直是身边版的梭罗本人。
这些生活美学,其实与他的课堂追求很一致,他的课堂,正在从那些课堂技术的追求里退出来,变得越来越不讲技巧,就像重剑无锋,或者朽木为刀,越来越接近于课堂教育本质:最为单纯的对话。而大概在15-17年之前,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,每次郭初阳有新课发布,我们都会为之惊讶不已,说他的课堂,便是一年一度的巴黎时装发布会,每一次都有新的看点、新的技巧、新的思想……团花锦簇,令人目不暇接,叹为观止。
曾几何时,江山不可复识矣。现在的郭初阳,居然变成了一个极简主义风格的践行者了。不太开车,步行为主;不事声张,低头做事;衣服倒还是穿名牌,只是商标几乎看不到。尤其看他现在写的文章,设计的课堂,实实在在,布衣素色,就好像这个作品里,就只有素材本身。郭初阳这个曾经的课堂上的超级巨星,去哪里了呢?
在郭初阳前一本书的前言中,有人说锅子是《瘦的郭初阳,瘦的语文》。这句话我至今认为颇得其中三味。人到中年,当然将来也许还有老年,不光光是瘦,甚至会是肉身干瘪——然而,越是肉体干瘪,不就越是接近一种纯粹的精神性的存在吗?这不就是人生的至境吗!随不能至,心向往之啊!
所以,中年版的阿老师喜欢“油尽灯枯”这个词,几乎超过“返璞归真”这个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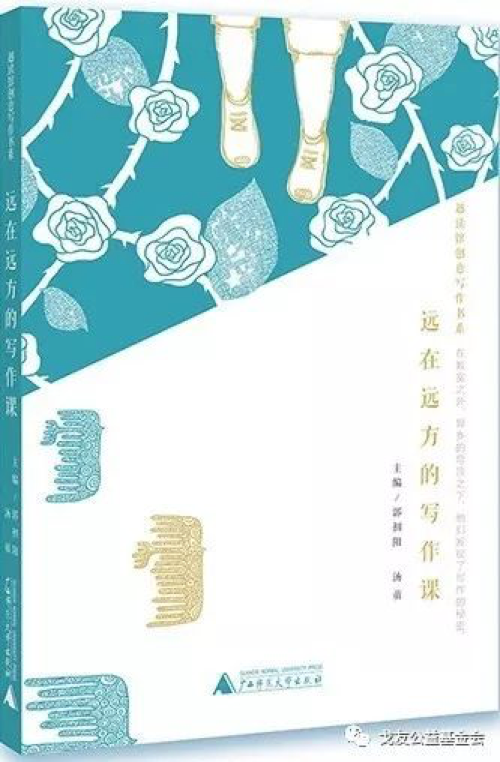
说起来我跟郭初阳认识,已经快有25年了。我们是大学同学,20岁初识,如今人到中年。生命越长,我们相识的时间就越长。
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师范学院做同学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,因为这其实只是一种萍水相逢——我们毫无来由地来到这个学校,毫无来由地被编在同一个班级里,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提着我们的脖子,把我们象棋子一样摆布。你要是真以为你的大学有自由意志的选择,那才是装外宾呢。就像四年之后,郭初阳被分配进了一个很小很不起眼的社区初中,而我流放到了另一座十八线城市,道理是一样的。这或许是某种象征,郭初阳很喜欢博尔赫斯的诗歌《棋》,里面有这么一句:棋子们并不知道其实是棋手/伸舒手臂主宰着自己的命运。
但即便在萍水相逢,偶然成为同学之间的空隙里,也还是有一定的选择自由的:我们有机会选择对方成为好基友!
我其实很寡情,绝大多数大学同学,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,从不遗憾,因为这无非就是萍水相逢。我不跟某甲在一个屋子里听课,就是跟某乙在一个屋子里听课。我们生活在一起,但生命并不交织在一起。唯有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,却成为了非常重要的、不可分割的存在,而与郭初阳,则简直是互为镜像。我不知道郭初阳怎么想,他性格沉静,喜欢假深沉,轻易不说心里话。但我是很确定的,要没有郭初阳和这几位朋友,我的现在可能也不是这样的。人生都是由细节构成的,一个细节不同,那么之后的道路便也不同。另外,人生,还是由朋友构成的,你的每个阶段的朋友,都切实构成了你的那一段生命本身。

我都已经忘了我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,最初是怎么接上头的呢,为什么那么多中文系的小金鱼小鲫鱼胖头鱼(李亚伟《中文系》),不跟这个人臭味相投,也不跟那个人相见恨晚,偏偏是郭初阳?
可能其中有一个非常共性的地方,就是对大学的想象的破灭。这个地方师范院校带给我们的失望是相同的。大概就是为了吐槽,才混迹在一起的吧。大一那年,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做了一件很异想天开的事情,从此顺理成章便成了一个精神共同体。
郭初阳曾经跟我说,他对大学的理解就是在,黄昏的时候,三五好友拿着吉他在草地上弹唱。而我呢,则以为,既然进了大学中文系,那么所有的同学都应该跟我一起来谈论古典诗歌。而事实与此完全不同,我们在黑乎乎的宿舍里嗑瓜子,在黑乎乎的食堂吃饭,在散发着僵尸气息的文艺理论课睡觉,最后终于找到出路:逃课。
如果没有郭初阳和这个精神共同体,我的大学会寂寞一万倍。也许是我们对大学的想象太浪漫了。那是1990年代最开始的几个年头,还带着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遗留,但现实的沉闷,令人失望。失望有时候是一件好事,就这样在失望当中,我们反而开始了自己的追索。大二到大四,我们读大量的书籍,既然课堂上学不到什么,那就自己学呗。
最近这几年,我跟郭初阳在母校中文系开了一门选修课。当年有一位我们喜欢的老师,几乎是唯一的一位——当时他还是资料室的图书管理员——担任了中文系主任,他邀请我跟郭初阳回中文系授课。于是,我们去了。
我与郭初阳愿意成为这门选修课的老师,可能基于几个共同的考虑。一则,对母校有感情;一则,对教育有想法;再有,或许是更重要的,当年无数节令我跟郭初阳恹恹欲睡的课,以及无数个我们逃课去逛三联书店的下午,我们最终发现大学在校外。但是,如果,那些大学课堂,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,而确实可能是有用的呢?也许,我们日后在幽暗中摸索的时间,就会少一些吧。

现在,我们这么想,校外的书店确实也很重要,但如果在大学的课堂里,确实有一些东西可以追寻,那么,这个大学才是我们更愿意称为大学的所在。之所以乐意开这门选修课,是因为,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课堂实践,把自己的生经验,以及职业生涯的一些体会,真实地去跟这些20岁的出头的,和我们当初一样的胖头鱼去讲述。也就是说,在我们那个时代,大学课堂跟我们即将展开的职业生涯和未来的人生,毫无关系。但一个从12年一贯的基础教育里出来的孩子,他真的很需要这些。
尽管我们在各种场合吐槽母校,但母校还是给了我们难以言述的馈赠,这也是我们深为感激的地方。不是说母校的学术训练给了我们基础,而是在黑乎乎的宿舍、教室,阴暗的资料室,远在本部的图书馆,这些个场合,给了我们建立精神共同体的机会,并让我由此结识郭初阳等几人。而我们这些人,带着对知识的饥渴,带着对理想的激情,在这个学校里相遇,最终,这种相遇,它将产生一些化学反应,产生一些潜在的作用,我们之前所不曾预料的,却从此深深影响你的一生的作用。
《诗经》里说,有匪君子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这个说法太斯文了,我们当时不像君子,却像嬉皮士。而多年之后,我们共同的朋友童蓓蓓则谬赞道:你们是双子星座。这个说法,虽愧不敢当,却沾沾自喜。
确切的说,我跟郭初阳应该是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。郭初阳,他有日本人的匠心,又有德国人的理性,这是两种非常奇妙的特质,在他身上却神奇地结合在一起,使他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特的气场、像标杆一样的存在。
我常以为,这种气质,在郭初阳身上聚合,是一种奇迹。一般而言,很少有人会有机会同时具有这样两种几乎悖论一般的气质。郭初阳之所以成为这个郭初阳,与这种气质是很有关系的。而我呢,跟郭初阳截然不同在于,我是粗放型的,任性、傲娇、随心所欲。所以,像我这样的人,一般不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,或者学者。但我热爱生活,所以总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,点亮唯一的生命之光。我不会成为学者专家,但我始终希望自己配得上做一个足够好的朋友。

按理,我和郭初阳两个人都是教师,总会有某些关于教育的共同话题。但是非常奇怪,我们之间关于关于教师、关于教育的讨论并不太多,甚而几乎没有。最多无非是一起编写一些读本资料,各抒己见而已。此外,尚年轻时混迹在一起,一般都是把酒言欢,三句不离中心论点:天下英雄,唯使君与操耳。“德也狂生耳”,现在想起来,尽管年少轻狂,倒也恰切。
20多年了,弹指一挥间。我们这些人,对教育的践行,其实应该有很大的差异了。比如我们选择的方向很不一样,他做他的课堂教育,按照他对教育的理解做越读馆。而我更多地侧重于学前教育,做儿童绘本阅读,作课外的游学活动。方向和事业的偏重完全不一样,但在基本的三观上,还保持着最为底线式的一致。但我想,这个事实,我跟郭初阳两人都会乐见。真所谓“渡尽劫波兄弟在,几度夕阳红”!
大概个人成长总要经历这么样的过程吧。如今,当年的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,两个高个子男生成了校长,漂亮女生成了教研员,而我跟郭初阳,则离开了体制。道路不同,而精神共同体尚在。我很感激有这些人的存在,也很高兴郭初阳自成一家,让我有机会写作文来挖他的黑历史,揶揄他、取笑他,而他大概只会淡然一笑,连尴尬都不尴尬一下。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奉行极简主义的人了。






